2025年,中国西藏雅鲁藏布江的墨脱水电站即将启动建设。这座规划总装机容量达60吉瓦、年发电量高达3000亿千瓦时的巨型工程,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。其不仅在能源产出上刷新纪录,也代表了中国清洁能源战略的一个里程碑。然而,碳排放接近为零的水电站清洁能源项目,却无法在当今的国际自愿碳市场中获得碳信用。这一现象背后,反映的是全球碳市场机制的深刻演变,也揭示了清洁能源开发与碳信用制度之间愈加复杂的关系。
一、水电的正面价值:从能源安全到绿色减排的基石
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一种,水电长期以来被视为低碳、高效、稳定的能源形式。与风电和太阳能相比,水电具有独特优势。首先,水电可提供全天候、连续的电力输出,是构建稳定电网系统的重要支撑。其次,水电拥有极低的生命周期碳排放,尤其是在替代燃煤发电方面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。更重要的是,水电还兼具防洪、灌溉、水资源管理等多重社会功能,尤其在地势复杂、资源匮乏的边境地区,有助于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稳定性。
以墨脱水电站为例,其建成后将为中国中西部、东南沿海提供大规模清洁能源支持,并成为“藏水入疆”等区域水资源调配战略的重要节点。从环境效益、能源结构优化到国家安全,水电项目无疑是中国推进“双碳”目标的重要抓手。
二、水电碳信用的辉煌往昔:CDM机制下的碳信用主力
在《京都议定书》设立的清洁发展机制(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, CDM)下,水电曾是碳信用(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, CERs)最大的来源之一。尤其是在2000年代,中国大量中小型水电项目成功注册CDM,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重要供应方。当时,碳信用市场关注的是“可计量、可报告、可验证”的减排行为,水电恰好满足这一需求。
那一时期的碳市场鼓励发展中国家利用清洁技术替代煤电,水电项目的“减排量”以其替代的高碳化石能源发电来计算,从而获得可观的碳信用收入。这些收入不仅支持了部分偏远水电项目的融资,也强化了清洁能源在全球碳治理体系中的地位。
然而,进入2015年后,随着《巴黎协定》的实施与碳市场治理逻辑的更新,水电在碳信用体系中的地位开始急剧下滑。根据UNFCCC的CDM注册信息,截至2012年底,约有1100个中国水电项目注册成为CDM项目,占当时全球CDM项目总数的21%左右。然而,到2020年后,无论是在CDM的遗留机制下,还是在新兴的自愿碳市场中(VCM),水电项目几乎被主流标准所剔除。例如,Verra的VCS(Verified Carbon Standard)体系中,2016年以后几乎未再批准任何新的大型水电项目注册;Gold Standard更是在2018年后全面限制大型水电项目的注册资格,仅在极少数具备显著共益性的中小型项目中保留入口。
与此同时,新的高质量碳信用标准,如ICVCM设立的“核心碳原则”(CCP),明确强调碳项目需具备强额外性、不可逆的长期减排或清除效果。这些要求进一步将大型水电项目排除在“高诚信碳信用”之外。
三、为何水电不再能获得碳信用?三大机制性转变解释其退出
尽管水电依然是重要的清洁能源类型,但在当前主流的自愿碳市场“高诚信碳信用”规则下,大型水电项目被普遍排除在碳信用资格之外。这一变化并非因为水电本身不再绿色,而是由于碳市场逻辑、方法学和标准体系的深刻重构。
第一,水电项目已无法满足“额外性”要求。
碳信用机制的核心原则之一是“额外性”(Additionality),即项目必须在没有碳信用激励的情况下不可行。换句话说,碳信用的存在应成为项目实现的关键推动力。
但墨脱水电站一类的大型水电项目往往由国家战略主导,拥有充足的财政、政策支持与技术储备,其建设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区域能源安全、推动绿色转型,并非依赖碳信用收益才能实现。这种情况下,即便该项目产生了实际的减排量,也因其本身具备强烈的经济与政策驱动性而被判定不具“额外性”,从而不具备碳信用核发资格。
第二,生态与社会风险与“共益性”要求存在冲突。
现代自愿碳市场不再仅仅看重减排量本身,更强调项目带来的生态与社会“共益性”(co-benefits)。这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、原住民权益、土地使用影响等。
大型水电项目往往建设在生态区,涉及大坝修建、河流改道、人工湖形成等,对当地自然环境可能造成影响。即便项目本身采取缓解措施,例如,雅鲁藏布江水电站通过“截弯取直、隧洞引水”方式开发,减少对河道生态的直接破坏,但其带来的生态变动依然难以回避。此外,水电站可能导致原住居民迁移、改变传统生活方式,甚至在跨境河流情境下引发争议。这些潜在影响均使得水电项目难以满足当代碳市场对环境社会治理(ESG)的相关标准。
第三,随着电网清洁化,水电项目的边际减排贡献日趋下降。
当前全球特别是中国电力系统结构持续优化,可再生能源占比快速上升,单位电力平均排放系数持续走低。在这种背景下,新增的水电项目所替代的“高碳电力”比例逐渐减少,其真实的“边际减排量”也随之下降。
尤其是在“统一电网”结构下,碳市场要求以边际减排为准进行测算,而非理论模型下的煤电对比。这意味着,即便水电仍可视作清洁电源,其实际替代效果远低于十年前的预期,因而所能产生的碳信用数量有限、价值下降。长远来看,碳市场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具有“新增减排”能力的项目类型,如直接空气捕集(DAC)、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(BECCS)等碳清除路径,而非传统的低碳替代路径。
总结:水电的意义重大,但碳市场逻辑已变
水电站,尤其是像墨脱这样的大型水电工程,仍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。其低碳、高稳定性的特征决定了它是未来能源系统中的基石。但碳信用市场的目标早已不仅是“减排”,而是追求“真实、可额外量化、长期锁存的碳效应”。
这意味着,碳信用的核发机制将优先支持那些在没有额外激励下不易发生、同时具备长期碳效益与社会共益性的项目。水电尽管环保、经济,但在机制设计的眼中,已不再是“稀缺性资源”。
因此,从最大碳信用来源到退出碳信用体系,水电的角色转变并非其减排效果被否定,而是全球碳市场对“信用”这一工具的定义发生了深刻转变。这种转变,既反映了气候治理的进步,也促使各类减排技术重新审视自身在碳经济体系中的定位。
正是由于传统减排项目在“额外性”和“减排稀缺性”上的边际效应递减,碳市场的重心开始向碳清除转移。与水电这类“避免排放”(Avoided Emissions)型项目不同,碳清除直接从大气中移除已排放的二氧化碳,实现的是负排放(Negative Emissions),被视为实现《巴黎协定》1.5°C温控目标的“最后防线”。
在全球尚未彻底摆脱化石能源依赖、且历史累计排放高企的背景下,仅靠削减当前排放已远远不够。碳清除的意义在于,不仅弥补了“减排不足”的缺口,更能通过“对冲历史排放”来弥合碳预算缺口。从科技路径来看,无论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(如森林再造、蓝碳生态系统恢复),还是基于工程的前沿技术(如直接空气捕集 DAC 或生物能源碳捕集 BECCS),都代表了未来碳市场的战略高地。
因此,在水电逐步退出碳信用的同时,碳清除正成为新的市场核心与政策重点。未来碳市场将不再仅仅是温和减排的工具,而是转向支持“实质性、大规模、永久性碳清除”的平台。这一方向的确立,意味着碳信用不再是对过去努力的奖赏,而是一种对未来气候安全的投资。

 切换行业
切换行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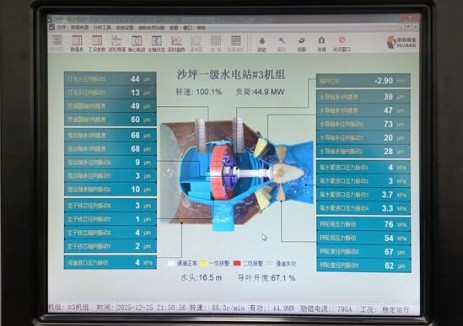
 正在加载...
正在加载...




